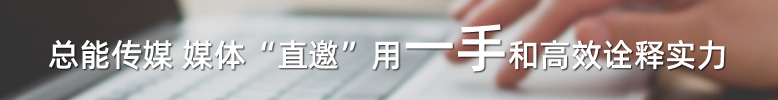B站“野居”青年新乡村生活的短视频实践
来源:时间:2022-08-17热度:0次
摘要
从媒介化理论出发研究B站“野居”系列短视频,探讨都市返乡青年如何通过短视频的媒介化展演重建“乡村乌托邦”,可以发现,“野居”文化的形成乃是三重空间的媒介化再生产:一是在地化乡村生活场景的“可视性生产”,即返乡青年通过具身实践所造就的一种可识别的“远离城市,隐居深山”的现实地方感;二是乡村田园景观的“可展示性传播”,即通过媒介技术裁剪、拼接、美化生活片段并上传至网络平台,形成可供观赏的乡村生活景观;三是集体怀旧的互动空间,网友们通过发送弹幕、点赞、评论等方式进行自我代入,使得“野居”不再是一种私人生活选择,而变为都市青年集体追逐田园梦的乌托邦诗学。因此,“野居”短视频是当代青年用媒介化手段象征性地解决生活“异化”的一种另类实践,但在技术、平台和资本的驱动下,野居生活最终沦为不得不进行的“现代性”工作——一种社会加速时代的“新异化”现象。
关键词
短视频;野居青年;媒介化;乡村乌托邦;新异化;
引言:短视频中的“乡村”
近年来,随着大都市生存压力的不断加大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返回乡村,用行动参与乡村建设1,亲身见证农村由“衰败”转向“新生”的实践变革。2在这个过程中,短视频等新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李子柒的田园系列到“滇西小哥”的云南风情以及丁真的川藏边陲世界,偏远纯朴的乡村生活和田园风景经由短视频这一媒介化手段呈现在网民眼前,引发无数年轻打工人的热议,甚至触动他们重返家园。相较于大量专注乡村吃播和农产品带货的短视频而言,“野居”3类短视频以媒介化方式重塑乡村美学,对抗物质主义主导的现代城市生活,它主要由一些逃离城市的青年人创作并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青年人为何要逃离城市回到乡村社会?为何要通过媒介化手段重新加工、制造和展演“新乡村生活”?经由媒介化手段建构的可展示的“乡村乌托邦”如何吸引大量粉丝的跟帖、留言和热议?粉丝又如何通过观看、跟帖和留言互动参与“乡村乌托邦”的再生产?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借助媒介化理论,以“Bilibili”(B站)视频平台上的“野居”类短视频为研究对象,探讨都市返乡青年如何通过媒介化展演重塑乡村田园景观,从而引发粉丝的热议和积极参与,共同建构和再生产具有集体怀旧情愫的“乌托邦家园”。最后,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反思了这种媒介化展演的本质内涵。
(一)研究理论与问题
在《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Culture on Display:The Prodution of Contemporary Visitability)中,英国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指出,在今天,“物件、场所和艺术品似乎越来越多地通过它们与人类关系这一视境来呈现。在此过程当中,它们应该被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近的。运用环境来交流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长久以来,乡村就被构造为‘景观’。在充满浪漫主义的注视下,它被传统地视作治疗都市现代性的药方”。4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媒介化环境下,包括乡村在内的物件、场所等都可以通过媒介化展演的方式加以展示和参观,借助媒介化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野居”青年的短视频创作实践。何为媒介化?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这样定义:
媒介化是这样一种发展进程,社会或文化活动(诸如工作、休闲、游戏等)中的核心要素采取了媒介的形式。5
换言之,随着媒介组织的发展壮大和独立性增强,“文化与社会逐渐依赖于媒介及其逻辑,而媒介则融入了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不同层面”6。“媒介及其逻辑”指向一种特定的传播形式,强调按照媒介的方式理解文化与社会。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新兴的媒介形式、媒介内容、媒介语法和媒介节奏全面渗透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像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数字媒介时代,在重新塑造日常生活的形貌中,在网络空间里集体展示的强烈兴趣将成为关键因素。比如,在脸谱网之类的平台的限度内,我们展示身份认同、开发公共形象或准公共形象。”7总之,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媒介化”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媒介化现实是一种人造而非技术决定的过程,强调人如何利用媒介开展日常实践,“通过提供新的可能性,媒介化改变了人类交往活动;而通过使用媒介,人类也改变了自己建构社会的方式”8。
回到“野居”文化现象,我们认为“野居”类型的短视频交织着三重空间的媒介化再生产:一是在地乡村生活场景的“可见性生产”,即返乡青年通过田园劳动等具身实践生产一种可见的日常生活场景;二是乡村生活和田园景观的“可展示性传播”,即通过技术剪辑、镜头拼接等手段对碎片化的乡村生活进行加工整理,并上传至社交媒体平台,形成可展示、可供观赏的乡村景观;三是粉丝的“可参与性怀旧”,即粉丝通过发送弹幕、点赞、留言和评论等方式“代入自我”,表达共情感受和集体性怀旧情愫,参与“野居”文化的再生产。正是粉丝的集体参与使得“野居”由极少数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选择演变为当代青年集体性的现代性怀旧和反思情绪。本文将对上述三重空间生产进行考察,即拍摄者乡村野居生活的真实体验、媒介化空间的视觉展演和粉丝参与地方文化再生产三个方面,探讨“野居”类短视频如何借助媒介化手段制造乌托邦式的“新乡村生活”。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之所以选择B站上的野居短视频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B站的内容特性和用户黏性。作为“年轻一代潮流文化社区”,B站以独具特色的弹幕语言和丰富多元的文化圈层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它的用户日均视频播放量达到13亿次,成为“国内用户粘性最高、承载这个时代‘唐诗宋词’的文化社区”9,同时也是许多青年UP主发布“野居”类生活短视频的第一站。自2016年开始,就陆续有“李子柒”“野食小哥”“巫托邦”“我们的小喜”“田园小漠”等青年博主在B站社交平台上传乡村风景和美食制作类视频。截至2020年末,B站已经聚集了众多从大城市逃离的“野居”青年博主,他们致力于在偏远农村开垦土地、改造农屋、种植花草、烹饪美食以重建远离城市的乡村乌托邦。
将“隐居”和“野居”作为关键词在B站平台进行检索,过滤掉企业、机构账号以及搬运、评述、讲解类等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得到播放量在50万以上的视频分别为“阿莫莎”的《改造山里小院,终于把房屋前后都变成了花海》(89.1万播放)和“野居青年”的《三个刚毕业的好基友远离城市,毁林开荒,隐居深山》(54.1万播放)。在观看两位UP主的视频后,B站播放页自动推荐了类似的视频内容,笔者根据视频创作者上传内容的年份远近、粉丝量大小、内容的区分度等标准选择了十位不同层级的UP主作为进一步观察的对象(见表1)。自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笔者对十位UP主在B站发布的短视频及其弹幕区和评论区的留言内容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断续观察,每次观察停留一个小时,记录视频特点和评论区互动情况,形成近4万字的观察笔记,同时收集了一些UP主在微博和微信上发表的言论及与之相关的媒体报道材料。基于上述文本材料的数据整理和质性分析,主要考察以下问题:“野居”青年如何讲述自己重返乡村生活的故事?如何通过剪辑等手段重新加工、制造和展演“新乡村生活”?粉丝又是如何通过观看、跟帖、留言互动并参与了“乡村乌托邦”的再生产?
重拾家园:恋地情结下的“回归劳动”
“和城市生活告别——收拾行囊奔赴乡村——择一处老房而栖”是许多“野居”UP主视频故事的第一幕。2017年,三位刚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绘画系毕业的大学生通过一条微博宣告了“野居”生活的开始,他们在B站开设了“野居青年”账号,自诩为“远离城市,隐居深山,三个男人的诗和远方”;2018年,一位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忽然卖掉陪伴了自己三年的自行车,回到家乡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随即注册视频号“巫托邦”记录乡间日常;2019年,一位叫“小雨的森林”的青年博主在B站上传了自己回乡建造“新家”的经历;2020年,两位宣称辞职返乡的妹子创建了“江山随食”的视频号,记录和展示她们爆改农村老房,过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野居生活情景。笔者根据视频创作者上传的内容选择了十位具有典型意义的UP主作为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
(一)恋地情结
厌倦城市和怀念乡村是现代性视阈下都市青年重返家园的重要起因。段义孚说:“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11“野居”青年基本都曾在乡村生活过。但在现代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他们为了谋生和发展离开乡村到城市里读书和工作。现在,他们厌倦了繁杂机械的城市生活,怀着对曾经的家园的眷恋重返乡村,“对故乡的依恋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它的力量在不同文化中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联系越多,情感纽带就越紧密”12。正是在重返的过程中,他们开始重新发现乡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由此重建自我与乡村、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返乡后,“野居”青年们往往在自己创作的短视频标题里突出他们生活空间和身份的转变——《90后小伙回乡下开荒种菜,逗狗喂猫,生活得逍遥自在》《80后夫妻,放弃城市生活,毅然成为返乡大军一员》《世界五百强白领裸辞后,回乡改造老房子之余学着种菜》……“野居”青年们并非是消极的逃离,而是以积极投身农业生产的方式重建人与乡村的关系,进而确立自我存在的价值。正如UP主“野居青年”所描述的:“只为自由,不问西东。”整饬家园、开荒种地和逗狗喂猫,体现的是乡村无拘无束、自由快乐的田园生活状态。
(二)回归劳动
“野居”短视频是对工业社会中人无法自由决定工作与休闲状态的一种反抗,回到乡村后,每个UP主都会宣扬“回归劳动”,声称这是出自内在需求的闲暇劳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需要——劳动——愉悦”的三位一体可以促进人性螺旋式的发展,成就一种“总体的人”的概念。13在丹·席勒(Dan Schiller)那里,“劳动不仅是物理的生产或形体的劳役,劳动更是人这个物种的特殊能力”,因此“回归劳动”又有了回归“人之自我活动的能力(the species-specific capacity for human self-activity)”(包括言谈与思索、行动与活力等脑力劳动)的文化意味。14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窑烧碗、粉刷墙壁、修理菜园、搭建花架,再亲手制作美食来犒劳自己,手工面、叫花鸡、槐花饭、鲜花酒,不一而足。对于“野居”青年而言,简单质朴的田园劳动孕育着美好,令人感到身心愉悦。“回归劳动”体现了返乡青年对日常生活本质的追求,因劳动实践而感到愉悦成为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所在。出于自身需要的乡村劳动实践与身不由己的城市打工谋生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是愉悦的、自然的,后者是被迫的、乏味的。段义孚曾说:“一旦人类社会变得复杂与精致起来,人们就开始关注和欣赏相对朴质的大自然了。”15现代性的主题之一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占据审美和道德上风的总是乡村。20世纪初,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主演的《摩登时代》已经将城市工厂劳动的机械乏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结尾处,卓别林主演的男主和他的心上人离开城市,向着乌托邦的田园归去。
(三)劳动创造美
“野居”青年回归乡村,重拾旧物,并非要回到当地农人的生活状态中,而是通过劳动实践创造美,即创造“新农村”。正是在回归劳动的乡村实践中,“野居”青年对其居住的乡村环境进行了艺术化和审美化的改造,让乡村以新的面貌出现:一方面,他们要让一切“修旧如旧”,老灶台、铁锹、旧箱子、充满年代感的收音机,经过他们的劳动之手,废弃的世界和破旧的老物件恢复原貌,走近旧物,仿佛回到了“过去”;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艺术家的想象力,让旧物重新焕发生命力和审美力。UP主“野居青年”会在春意盎然的时节描一幅《院墙前的油菜花》,在绿树成荫的夏天再绘一幅《盛夏的杏》,在大雪封山之时画一幅《雪中小院》,用石棉瓦搭建围墙,要在上面画满手绘风景;修一面泥墙,要取个诗意的名字“东篱”;用砖和茅草建造厕所,要精心涂鸦,命名“伦敦眼”……破败的、过去的和老旧的世界经他们之手焕发生机。“野居”的乡村诗学就在现代性层面被审美性地建构出来,成为一种“未来的过去时”:
重拾旧物,既钩沉历史价值,亦抉隐身体感受。这一审美机制既有绿色意义,更具开放潜能。生活旧物彰显的物质美学,绝非怀旧乌托邦或消费理想国,而是以物质为方法,眼光向下,在发展与进步的城市化进程中打捞着“未来的过去时”。16
UP主“野居青年”的画作有时会以赠予或出售的形式寄给粉丝观众,在回答粉丝困惑时,他们反复强调回归田园并非要放弃舒适的现代生活:“很多人说我们在山上修仙,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并没有任何想要跟外界隔绝、断开联系的想法。”
可供性“慢生活”:被展示的乡村景观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曾感叹:“现实的乡村从来与风景无关。”17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农人不会将眼前的土地和房屋视作风景,更无所谓的“乡愁”,只有进入文学、绘画、建筑、摄影和旅游等一系列现代文化实践中,乡村才被建构成满足视觉审美和观看愉悦的艺术品。18廖新田在检视台湾近现代视觉艺术发展中本土意识觉醒时亦认为:“以‘怀旧之美’为例,美不在‘旧’之中,而是藉由现代的凝视,即‘纯粹’的视觉(the‘pure’vision)所启动。易言之,只有用特殊的眼光才能发掘乡下朴实之质、斑驳之美。所谓真挚之心也只不过是现代情境下的‘虚骄讹见’。对一农夫而言,夕阳西下的归牧心境,和浪漫诗意是扯不上关系的,除非此人具备解读乡土的符码,并当下转换心境。”19
在一个时空被高度压缩的现代性社会,人们已经很难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偶尔短期的乡村旅游往往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网络社会兴起之后,“因特网提供了一种新的‘延伸的场景’的机制化,在其中不是时间,而是空间有了优势”20。B站等社交媒体平台让乡村成为随时可交流、可储存、可欣赏的“可供性视听景观”。
社交媒体通过聚合用户及其网络(例如,Facebook关于用户画像的“About Me”部分)发布的内容使信息变得更加可见。搜索功能使定位信息更加容易;通过这种方式,社交媒体提高了可见性(visibility)或者说“可搜索性”(findability),与其他数据存储过程相比,这种数据损坏的可能性更小。21
乡村被“可见性的展示”是社交媒体时代乡村出场的重要背景。与传统文人追求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有所不同的是,当代返乡青年虽逃离喧嚣都市,重返质朴乡村,却并不甘寂寞。相反,他们乐于在B站、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私人视频账号并公开展示“野居”生活,所“展示的乡村”也是媒介化技术剪辑和拼贴出来的片段化、碎片化乡村景观——一种可供性“慢生活”。虽然同样参与垦殖耕耘、修葺房屋、烹饪三餐等日常劳动,但这种生活迥异于当地农民真实的日常生活,而更像是城市生活世界的空间延伸,如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这种风格化是有系统的决定,它支配和构成各种各样的实践,如选择一个酒类制造年份和一块奶酪,或装饰一座乡间房屋。”22
(一)发视频,分享生活
作为纪录类的短视频影像,“野居”青年的短视频拍摄并非是对乡村生活场景的完全复刻,而是有意识、有策略地对内容进行媒介化手段的处理,那些令人不悦的或具有冲突性的镜头通常被删除,充满美感、令人愉悦的乡村事物得以保留。大部分青年UP主声称“野居”就是要让生活变得更浪漫美好,如果真要跟外界切断所有联系就不会“发视频,分享生活”。
很多人觉得我们的视频很治愈,我想我们最大的价值亦是如此了。在这样重压的环境下,能让陌生人感到生活的美好,这就是意义。23
因此,“野居”短视频其实是“展示的诗学”,关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片段被选择性地重新剪辑再上传到B站等社交媒体平台。勤俭、乐观、环保的正向精神状态被着重展示,繁重乏味的劳动过程及作物漫长的收获期被压缩展示。“巫托邦”耗时三个星期建造茅草屋的过程被压缩成累计八分多钟的三个小视频,“满叔的院子”历时三年打造1000平的花园小院做成视频只有不到五分钟,“我们的小喜”历经两万次捶打和多次失败制成的手工茶盏最终呈现给观众的只是做成功的那一个……显然,能反映阶段性成果的、具有生活趣味性、视觉观赏性的作品才更有可能被“野居”博主上传至平台,万物生长、房屋建造和日常劳作的冗长过程一带而过。正是通过精心筛选和浓缩的视觉镜头,“野居”短视频讲述了一个关于“慢生活”的美好田园故事。吊诡的是,短视频恰恰是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产物,所谓的“慢生活”需要过滤掉大量琐碎无聊和缺乏美感的生活场景,保留值得观看和可供欣赏的乡村景观。
(二)程式化的视频生产
现实场景在数字化图像技术的介入下不断变得非现实化,生活场景转而按照视觉预设和观众预期的方向进行组织和发展,这是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强调的媒介技术的审美化,也即现实生活逐渐按媒介图式来构造、表述和感知的过程。24虽然“野居”UP主们都强调自己更多的是“记录真实生活”,但是未经媒介加工的日常生活往往是无聊的重复,而短视频要求的是寻常但可变的欢喜。一些播放流量较高的生活题材受到关注,而它们也给“野居”生活剧本提供了可以模仿的范本。借助范本,媒介化、工业化和程式化的野居视频很快被生产出来。2021年3月,“野居青年”第四次宣布《我们又又又又找了一个新院子》,在网友眼里,他们早就是“基建狂魔”“戏精”“房东笑醒”等话题的制造者,因为粉丝从他们改造房屋的视频里总能收获变废为美的惊喜。2019年7月,“巫托邦”开始发布“抓住夏天的三十个计划”系列视频,主题是“带大家一起做那些曾经在夏天想干而不敢干的事”。25该“计划”深得粉丝喜爱,于是“巫托邦”在2020年又陆续推出了“夏天计划”“冬日计划”,以形成“野居”生活的固定程式。
如此看来,“野居”青年的“慢生活”有根据流量喜好进行定制的倾向,他们在快速复制“乡村生活剧本”的过程中呈现慢生活的精致潇洒。这些程式化、类型化的“野居”视频,将日常生活的精致呈现与视频中的角色风格融为一体,其实与工业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并无本质区别。
(三)多元组合的镜头语言
“野居”短视频中的乡村景观和田园世界之所以打动人,得益于镜头语言的多元组合,即通过场景调度、色彩调配、蒙太奇组合等多种手段对乡村生活进行重新构建。例如短视频中有大量对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的综合运用。钱钟书曾经论述过“通感”,他认为:“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26
这种“通感”被巧妙地置入到短视频结构中,“油溅到我身上了”“烫到我了”,经由粉丝的弹幕留言、评点,“通感”让人们重新体会到了乡村的日常和烟火气息。这时,短视频中的生活之“慢”不再是基于时间观念,而成为某种视觉修辞,即相对于庸常乏味的现实生活它是“快”的,而相对于压抑快速的都市节奏它又是“慢”的,是一种速度可控、细节可寻、声音可辨、味道可感的诗意栖居生活。又如,“野居”短视频试图通过多重地方声景的重塑唤醒人们的乡村记忆。这些声音多是“自然之声”——鸟鸣春涧、风吹毛竹、花开花落和雨打芭蕉等,配以舒缓的背景音乐和声音特效,营造出一种不受外物打扰的山野幽居的怡然自得。当然也有“巫托邦”这样的UP主以风趣的话语引领观众去领会幽居之美。在这些声音地景中,偶尔还会浮现当地的方言对话场景,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以冷色滤镜烘托自然风景的清新明亮,以复古滤镜展示旧物的文艺精致,以高饱和的黄色滤镜衬托食物的美味可口;用镜头回放制造“隔空取物”效果等等。实际上,在这样的展演书写中,自然的乡村已被镜头化、细节化和蒙太奇化。但这类镜头的处理,恰恰为观众提供了观看和体验野居妙处的多重路径。
互动参与:“野居”诗学的集体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中,中国的乡村经历了从短暂繁荣到田园将芜的过程。2009年,《南方周末》刊发了主题为“荒芜的家园”的图文新闻报道,纪实展现的是衣服还挂在斑驳的墙上、窗户上还挂着一只空鸟笼,但屋子里已是人去楼空的荒凉情景:
这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破败的农舍,墙体布满苔痕水渍,一扇木窗空洞地开着,左上方挂着一只竹编的鸟笼,右侧则挂着一件穿脏的衣服,仿佛,它们在焦虑地等待着主人的归来,可以想象这里曾有过多么生动火热的生活。如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多少农民抛弃了原有的一切,奔忙在进城打工的路上。当我走进增城正果镇这条叫作秋风坳的村子,看见这样的场景,心头顿然生出隐痛与担忧。27
这是当时中国乡村的普遍景象,正是城市化、工业化导致了家园的荒芜和乡村的空心化。近年来,国家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建设又得到重视。除了对“996工厂”生活的厌倦和恋地情结之外,“野居”青年返回乡村,开展重建乡村的行动实践,其背后也有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引导。作为一股新社会潮流,目前这种零星的“回归”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示范价值。在短视频等新媒体的赋能下,“乡村”重新被赋予自然和生活诗意的可见性,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情感共鸣。B站“野居”UP主的记录与展示能够在视频转发和弹幕互动过程中营造一种有关“诗和远方”的共情空间,突出一种向内追寻生命的本体意义、向外激发乡愁怀旧的集体情感。这种表达所击中的恰恰是当下青年人试图摆脱“现代性焦虑”、回归传统价值的普遍“情感结构”。28
(一)“为我们存在”的意义生产
对于生命本体的关怀一直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野居”故事文本的核心主题便是生产并张扬一种“关怀自身”的生命状态。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主张“一种贯穿于身体与思想精神两方面的生活风格,一种以‘关怀自身’为中心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的技术”。29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所倡导的“日常生活人道化”亦强调日常生活应该变成“为我们存在”,她认为幸福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有限的成就”意义上的“为我们存在”:
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为我们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都能够持续地得到更新,我们是在过有意义的生活。30
“野居”青年便是通过短视频媒介努力建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UP主们从都市圈返回乡村,回归劳动、融入田野,重建自己与乡村的关系,甚至将乡村视为自己身体和精神的最后归宿。他们也通过与粉丝互动,将乡村建构为具有集体记忆的文化共同体。因而,“野居”短视频不仅“关怀自身”,而且“关怀他人”。就笔者的观察来看,粉丝的参与互动至少从三个方面推动了“野居”文化的再生产。
其一,通过对视频内容的追问拼凑出完整的“野居”故事,以达成对野居生活意义的共识。“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你们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你们的收入来源是什么?”是粉丝普遍好奇的问题。“野居”博主往往通过视频独白、回复留言等方式来回应。“野居青年”最早的回答是“纯粹出于自己喜欢,向往这种生活”以及“大学时期带美术考前班的积蓄”31;“江山随食”回应自己返乡是为了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由于乡村生活的低成本、低欲望和“新鲜感”,所以并不太担心经济来源问题32;“满叔的院子”透露自己曾经作为知名摄影师的身份,漂泊多年后“想要寻找内心的归处”,建好院子后仍从事摄影创作来赚取收入,并表示“这个时代到处都在传递焦虑,而我只想对你贩卖人间美好”33。
其二,通过发弹幕或留言对UP主和视频内容表达喜欢、提供意见或代入自我,抒发关于理想“野居”生活的共情感受。事实上,粉丝们对“野居”系列短视频的情感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艳羡UP主能够过上脱离城市喧嚣的理想生活,由衷地发出“这才叫生活啊”“我曾经的梦想你们帮我实现了”“希望你们永远如此”的感慨;34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励甚至怂恿UP主进行商业化运作,以确保这份“美好”持续运转。有些粉丝通过留言呼吁“野居青年”接广告,“接点广告吧。最起码不要被家里说,老家那里不挣钱的事情都被看作是游手好闲”“广告其实可以接的,你们基本生活也要维持,现在你们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很大吧,加油”,也有粉丝建议通过商业化、“个人存在感与价值感的宣扬”来实现田园生活意义的最大化。他们深知“在理想的房子里,这里既是生活也是工作”。35
其三,通过加入部分UP主搭建的基于园艺、建造等主题的兴趣群开展深度交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野居”理念。例如“江山随食”建立的“随时小筑和它的朋友们”微信群,目前有100多位粉丝加入,他们在群里讨论UP主的视频,交流美食制作、庭院建造、花卉养殖的经验,偶尔也会对喧嚣城市生活予以评价,以起到缓解压力、抱团取暖的目的:“房子是租来的,但日子不是租来的,加油,你们俩。”“自从来了上海拼搏,空闲时间好少,好想有空给自己放个假,去江山过下自己想过的生活。”“静水的山谷花园”组建了“静水花园种子分享群”,为300多位粉丝提供分享园艺快乐和种植心得的平台,同时采纳粉丝建议,发起了花卉种子的线上“认领”活动,给全国各地的花友们寄出了1600份自己亲手采集的种子。群友“太阳”感慨道:“好喜欢这个群,找到了快乐老家,身边都没人养花。”
粉丝积极广泛地参与交流讨论,不断续写和再生产关于“理想生活”的现代性反思故事。“野居”也由此从个体层面的“避风港”变成了大众层面的“精神家园”,激发了广大网友努力去过“为我们存在”的“有意义生活”。
(二)乡愁怀旧的集体记忆
“野居”青年关于在B站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诗和远方”的视频记录和展示,激发了粉丝对家园的集体怀旧情愫。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这种怀乡病是全球性的。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llana Boym)说:
不知为何,进步并没有医治好怀旧情感,反而使之趋于多发。同样,全球化激发出对于地方性事物的更强烈的依恋。与我们迷恋于网络空间和虚拟地球村现状对应的,是程度不亚于此的全球流行病般的怀旧;这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渴求,在一个被分割成片的世界中对于延续性的向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快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36
从深山定居到房屋装潢,“野居”空间的一砖一瓦,一花一木,全都有种“做旧”的味道——茅草屋顶、卵石鱼池、竹制篱笆、青砖铺路、枯木养花……还有“过时”的橱柜、书桌、电视、游戏机,各种挪用、嫁接和拼贴的怀旧细节,打造出复古而文艺的乡村生活空间。视频怀旧空间的复建还原事实上唤起了粉丝对消逝的童年和家园的集体记忆。“怀旧——英语词汇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词语,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是对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36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孩提时代的回忆“发展了重返过去并在想象中重温过去的能力”,而“沉思冥想的记忆或像梦一样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社会”。37“野居”短视频激发和点燃了粉丝的家园怀旧之情:“怀念这样的日子,可惜生活太忙了,回不去。”“我曾经的梦想你们帮我实现了。”比如“满叔的院子”发布《这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夏天呀》视频,粉丝感慨:“怅然间总有回到过去的错觉。”“这也是我的梦想,一个山下的小院,齐眉的屋檐,四季的香树,清澈的池水,浪漫的图书,远处的深山。”38随即在评论区晒出儿时看过的动画、听过的歌单、生活过的风景和做过的傻事,个人记忆和媒介记忆交织在一起,形成“真的回不去了”的集体感叹。“阿莫莎”仿照宫崎骏动漫《哈尔的移动城堡》改造的手工坊获得了上百万的播放量,其还原度令网友惊呼“厉害”“太棒”“喜欢”,粉丝们既欣喜于“总有人替我们把日子过成童话的”,又感怀于“人老的好处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39
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乡愁”与城市化、现代人际关系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它具有一种将‘过去’乌托邦化的强烈的情感色彩”。40在“野居”短视频中,富有仪式感的美食烹饪唤起了网友们对“过往”的生命记忆,这些回忆通过弹幕文字延续乡愁记忆。2019年春节,UP主“野居青年”穿越秦岭,回到故乡,连续三期发布了在陕西汉阴老家和爷爷一起度过的时光,画面是井井有条的菜园子、烟熏的豆腐干和腊肉、步骤烦琐的“苞谷酒”,如此牧歌般的田园景象瞬间激发出粉丝们的“乡愁”,让他们有了“代入感”。网友“Ayakamiki”动情地留言道:
多陪陪老人家,我爷爷04年就去世了,虽然那个时候我才8岁,但是我对我爷爷的记忆还是恍如昨日一样……如果你们也家里有老人我想说多回家看看吧,别让等待成为遗憾。41
曾经许多人拼命逃离的落后乡村,在“野居”短视频的展示与召唤结构中,瞬间成为个体记忆中魂牵梦萦的“诗和远方”,只是抛开乡愁表象,这个“远方”更像是浪漫化的乌托邦愿景。博伊姆在讨论现代性反思语境中的怀旧时指出,怀旧的危险在于它倾向于“混淆实际的家园和想象中的家园”,42在粉丝的理想设定中,回不去的故乡其实是撇去了粗糙环境、复杂人情和繁重劳作之后的美丽家园。
综上,“野居”短视频的魅力在于它的空间构造中重叠着三度景深:一是逃离城市、回归田园以找寻内在生命意义的具身实践空间(视频之外场景),二是通过媒介技术手段再现乡野“慢生活”的情境化空间(视频文本场景),三是在前两者基础上所衍生的关于怀旧和乡愁的集体互动空间(视频观后的互动场景),这三重原本疏离的空间借助媒介化的社交平台得以交汇重叠,共同搭建了一个可寄寓集体怀旧情愫的乌托邦家园景象。在这样的观看框架和精神寄寓空间中,乡村及其生活都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但究其本质而言,这套观看乡土风景的框架和方式仍然是现代性的、都市性的和媒介化的。
社会加速时代:从“异化”到“新异化”
微信公众号“新世相”曾发起过一次调查,询问订阅的粉丝“希望18年后的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收到的几千条回答里,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幻想自己“英年早退”后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43“996”的工厂生活、油盐酱醋的日常开支、买房买车的高额消费、动辄猝死的健康风险都是当代青年人不得不面临的生存境遇。“用工作来挣闲暇”“闲暇只为离开工作”的恶性循环成为许多年轻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异化的劳动关系和生活状态,带有乌托邦色彩和自然美学情调的“野居”突然成为一种逃避方式,也可能成为一种青年人重新发现自我和乡村的文化潮流(当然这种新社会潮流本身也得到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引导)。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则从社会生产关系、个体存在价值以及技术环境变化等诸多层面对人的自我发展进行了剖析,也为批判性地认识当代都市青年返乡生活的媒介化表达提供了理论资源。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日常生活是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一切人类生存和历史的基本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4因此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从人类文明的演变来看,在人的依赖性社会,由于人类生产力有限,日常生活基本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全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进入物的依赖性社会,日常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原本属于个人的生活领域,被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渗透和支配着”,“非日常生活取代日常生活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方式”。45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异化劳动”意味着“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44列斐伏尔将对“异化”的观察从宏观的生产层面降至微观的大众消费和日常生活的层面,彰显出后工业时代的人文关怀。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元素(工作、家庭和“私人”生活、闲暇活动)的分离即意味着异化,而闲暇之所以脱离日常生活是因为现代技术发明了一系列“闲暇机器”(收音机、电视机,等等),令人产生了一种可以随意摆脱劳累和紧张工作的错觉。事实上,这种所谓的“闲暇世界”只不过是纯粹人为的、密切模仿现实生活但又脱离日常生活范围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虚幻反转形象王国”,使得本该处于日常生活领域的休闲娱乐异化为了“非日常生活”。46这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后来对消费社会的观察类似,由图像与景观充斥的日常生活实则处于一种技术的操纵之下,“失去了日常生活原本具有的自由、自适、自在和自发的特征”。47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日常生活的“异化”呢?列斐伏尔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都提出了“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概念,主张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用一切技术手段来改造生活。”48这里的“改造”并不局限于艺术品,而是意味着一种自我意识的再生产,并使其与自身的身体、欲望、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相适应,成为自我的创造。这就意味着今天的革命不再是指向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阶级斗争,而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摧毁迷人的景观,以建构真实的生存情境”。49
在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构建的“野居”空间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以上关于日常生活方式变革的可能性——离开繁华都市,寻一处僻静土壤,除草垦荒,种花造物,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成为这群青年UP主的一种文化和艺术自觉。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成为自洽闲适的个体,并在艺术化的改造中赋予生活以审美感和愉悦感。然而,这种打破日常生活“异化”的实践经由短视频的媒介化展演沦为一种“拟态现实”,使得“野居”一方面可作为理想生活的实体空间(符合田园生活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可作为数字技术加持下网络文化展演的符号空间(具有流量变现的经济潜力)。这种“双重勾连”关系下的日常生活革命到底是“真实生活”的体现,还是“媒介景观”的展演?由此看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能否真正消除生活的异化是值得怀疑的。
结语
本文从媒介化理论出发,以B站“野居”系列短视频为研究对象,探讨都市返乡青年如何通过短视频的媒介化展演重建“乡村乌托邦”。通过研究发现,“野居”文化的形成乃是三重空间的媒介化再生产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情况下,短视频作为社会建构的重要媒介手段,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发现社会(城市/乡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野居”系列的短视频以反叛机械复制社会的姿态出现,但从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来看,在技术和资本的驱动下,“野居”类短视频其实也是数字时代文化工业的一种,受技术、算法和商业消费需求的支配,看似潇洒的返乡行为背后是另外一种“新异化”。总体来看,从“异化”到“新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野居”开启了摆脱“异化”的可能之门,那是一种不需要很高的物质成本就可能岁月静好的生活,“回归生活”冠上了诗意的光环。对于“野居”系短视频的粉丝而言,归园田居应该是纯粹的不以逐利为目的的理想生活:“B站有很多主打田园主题的视频,可是田园外壳下都是泛滥的广告、猎奇的内容、迎合大众的审美,这不是真正的田园,这是工作,这是他们生存的工具。可是我在野居这里看到了生活,看到了对于自我精神园地的坚持。”50
另一方面,作为生活美学的“野居”虽“凭借新技术缓解了消费主义导致的人与人间的疏离感、商品拜物教和符号化倾向,也在创造着一种生活艺术和日常生活重构的希望”51,但作为短视频文化现象的“野居”,正逐渐沦为平台流量和商业软广裹挟下的数字景观。无论是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抵抗还是提供“诗与远方”,作为一种“被展示的景观”和一种依托于平台经济的数字产物,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不过是资本和媒介技术合谋下的一种“文化奇观”,是日常生活的重新“异化”。为了生存,许多“野居”系博主逐步走上平台为其设定的道路——商业转型和流量变现,如发展民宿、贩卖农产品、植入广告等,自适的生活美学逐渐向审美化的空间消费转变,日常生活本身不再是最终目的,而是沦为赚钱的手段。甚至“野居”UP主的每一次创作与粉丝观众的每一句评论都已被卷入商业利益的漩涡。
在平台和数字资本环境中,每一个心怀“向往生活”愿景的创作者和消费者都以“数字劳工”的形象被吸收和转化,所谓的“野居”短视频文化不仅仅是被营造出的“乌托邦诗学”,也是披着情怀外衣且可以不断增值的数字产业。视觉时代的来临若使生活本身沦为被展演的商品,所谓的“文化革命”也将失去其原有的意义。
下一篇:媒介融合专题解析